紫砂壺工藝發展
紫砂壺藝術是反映時代風尚的產物,歷代紫砂藝人在細心觀察和研究社會現象及自然形態的基礎上,吸取了中國傳統繪畫和古代陶器、漆器、玉器、秦磚、漢瓦、唐鏡、瓷器等傳統工藝美術品的藝術特點,從而表現為由粗趨精,由大趨小,由簡趨繁,復又返璞歸真的過程,即經歷古樸、華麗、淡雅三個階段。
據文獻記載,紫砂壺在草創期,“金沙寺僧逸其名,聞之陶家云;僧閑靜有致,習與陶缸翁者處,博其細土,加以澄練,捏筑為胎,規而園之,刳使空中,踵傅口柄蓋的,附陶穴燒成,人遂傳用。”(明代周高起《陽羨茗壺系》)。這個和尚沒有留下姓名,因而引起后人的追念。吳騫有詩曰:“金沙泉畔金沙寺,白足禪僧去不還。”這個“白足禪僧”,就是紫砂茗壺的創始人。紫砂泥的可塑性非常好,而到了供春時代,在草創期老僧以“捏筑為胎”,供春卻“茶匙穴中,指掠內外”。供春又變革研木為模,這是制壺工藝的一大改進和提高。“研木為模”的模具,它是一個內模,泥胎在木模上奎制成型,這個方法傳至時大彬,“時悟其法,則又棄模”,“時乃故入以砂練土,克諧審其燥濕,展之名曰土氈。”(周容《宜興瓷壺記》)。時大彬領悟其制作方法,不用模具制作,練好土,掌握好泥的干濕度的泥性,把泥打成泥條、泥片來成型。“割而望諸月,有序先腹,兩端相見,廉用媒土,土溫曰煤,次面與足,足面先后,以制之豐約定。”這段說的是:把裁割好的泥條,以腹徑圍在木轉盤上,用拍子拍打兩端,先足后口面(滿),用脂泥黏接底片和口片(滿),這樣制成壺體的毛身筒。“次開頸、次帽、次耳、次嘴、嘴后著戒也,體成”(周容《宜興瓷壺記》)。在整理好的壺體上制壺頸、壺蓋、壺把、壺嘴,完成整個壺體造型。
文獻的記述,就是我們現在的打泥條,打泥片,拍打身筒或鑲接而成的成型制作工藝,一直傳承至今,并把這種傳統的制陶技法保持非常完整,且有提高和深化,為其它民間工藝所少有。這具有科學規范的傳統工藝技法,作為我們當代制壺人來講,應在這基礎上發揚光大,要具備開拓進取精神,為弘揚紫砂文化而不受其它怪談、玄說所困惑和貶褒。下面把我去年新創作的一把《器成方圓》壺和廣大壺藝愛好者交流一下創作過程和意念。
《器成方圓》壺,實話講,沒有規矩,不成方圓,天為方,地為圓,且說天地方圓,本人完全是從古樸、端正、穩重等指導思想出發,大膽嘗用建筑學、力學和各種幾何形體相結合,并采用先祖所遺傳的打泥片鑲接而成的方法,共計用了十三塊泥片,鑲接而成的壺身以兩個正方體為曲面,而實際整體為一棱形體。壺嘴為一大一小圓柱體而成,壺把為一個圓柱體和兩個梯形鑲接而成,并配以傳統的牛蓋作為裝飾,造型簡練大方,于平淡中含濃烈,平易中顯示新奇,一如人品,質樸自然,剛正而不俗雅。
綜合上述,紫砂壺的造型“方非一式,圓不一相”,千姿百態,層出不窮,真可說是一座造型的寶庫,從而以設計意識為主導,伴以形象思維的審美意識,通過工藝材料、工藝手段和各種專業技巧進行制作或發展的一種藝術。它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純美術。其本質特點是強調實用價值、審美價值和功能性的統一,具有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屬性,所以紫砂壺造型藝術作為融生活與藝術為一體的文化形態,是中國民族文化水平的形象寫照。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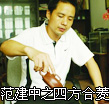

 紫砂壺名家邵順生老師
紫砂壺名家邵順生老師 紫砂壺名家之湯鳴皋
紫砂壺名家之湯鳴皋 高級工藝美術師吳芳娣
高級工藝美術師吳芳娣 高級工藝美術師錢祥芬
高級工藝美術師錢祥芬